我滿臉淚水,漫無目的地在北京的大街上晃悠,路上的行人投來了奇異的目光。
那時的我真的是豁出去了,只要能透口氣,我願意這樣被人觀望。
衣袋裡的手機不停地響 ,我知道是曾凱打來的,他一個大男人哪能整住一個軟綿綿的小可愛,可我就是想讓他體驗一把帶孩子的辛苦。
都喊累,都喊苦,女人不苦嗎?我內心的那種失落不知該給誰講,可選擇當了母親我就得扛起身上的那份責任,走累了,我也想明白了。
離開職場只是暫時的,我終究會回歸,只是老公是自己選的,婚姻是一輩子,一點小事就看出了端倪,可箭在弦上,已無法回頭。
我抹了一把眼淚,鎮定了情緒,推開了門,曾凱狼狽地坐在那裡。
兒子呵呵地笑出了聲,不知是在迎接我,還是看到他那不靠譜的爹那個囧樣子。
曾凱看到我回來了,就像是迎來了救星,一個勁地給我掐腿揉胳膊,生怕我會撂挑子。
那天晚上,我和他深談了一次,我讓他不要光會賣嘴巴皮子,干點實際的活,這個家是我們一起共擔的。
他也承認了錯誤,這個是他的強項,談戀愛時我就知道,不管對不對,他都會先服軟。
我質問他曾經的承諾,家務活全包哪裡去了?他無言以對,可他也說了自己的委屈。
他說他壓力大,換了新領導,天天捉摸著如何不踩坑,哪有心思做家務!
我氣得一個抱枕扔過去:「你不好好工作,竟想那些沒用的幹嗎?
你管他誰來當領導,你一個技術男,靠技術吃飯,你和人家比什麼比,少整那些沒用的」。
那兩天,我不怎麼和他說話,就想晾一晾他。我一直堅信困難只是暫時的,一定會熬出去的,不知是曾凱動了歪腦子,還是我媽想我了。
在那個陽光明媚的午後,我媽竟然提著行李,獨自站在了家門口,說自己在家閒著沒事,想過來住一段時間,看看孩子。
我媽啥也沒說,我也沒再問,只是曾凱下班後竟然哼著小曲進了門,一聲聲媽叫得那是個親呀。
我媽說她一個人寂寞 ,來北京就不打算走了,也好幫襯我一下,可我很擔心我媽的身體,我不想讓她累著,可她總是搶著活干。
天下的媽媽可能都是如此,生怕女兒受了委屈,我媽的到來,確實讓我輕鬆了不少,能吃上媽媽做的飯,我感動得流了淚。

大學四年,我為了攢學費,又怕浪費路費,我都不怎麼回家,但媽媽做的可口飯菜我從來都沒有忘記過,紅燒肉,豬蹄膀、豆花飯、粉蒸肉,哪一樣都是我最愛吃的。
婆婆家是山東人,除了烙餅子,就是大蔥蘸醬,偶爾炒個菜也沒有顏色。生活很不講究,曾凱也隨了他家。
做飯根本沒眼看,做家務馬馬虎虎。至於他那個狗屁承諾我只當他是為了表真心,就那樣他還不當回事。
曾凱見著我媽,可是逮著機會表現了一番:「媽,您能留下來幫我們,真是太好了;以後,這裡就是您老的家!以後我不光是你女婿,還是你兒子,你隨便差遣,隨便打罵!」
說完,我們三個人都笑了,冷漠了幾天的氣氛一下子變得融洽。
有了我媽幫襯,管孩子和家務活都安排得妥妥帖帖,我真是輕鬆了不少。
我也不再嘮叨曾凱了,他天天都偷著樂,還不忘謬讚我媽幾句。
他也不是個蠢人,知道分寸,每天回到家,他都會假模假式地鑽進廚房,不是剝蒜就是剝蔥,可是會討好我媽,能把我媽逗得樂呵好一陣。
他常掛在嘴邊的經典名句:「老婆,你媽就是我媽,女婿就是親兒子,你放心,我以後一定會孝順咱媽的!」
如果日子一直這樣幸福下去,也許我們曾經的約定還會實現,只可惜,曾凱的大話一出,考驗他的時候就來了。
那天,我媽照例下樓去買菜,可剛一出菜市場,就暈了過去,好心人撥打了120。
事情來得太突然 ,我接到電話差點嚇暈了過去 。
我媽被送到醫院後,診斷為主動脈血管夾層破裂,病情兇險,醫生建議立刻手術。
我哭得泣不成聲,看著眼前晃悠的白衣天使,我多想揪住他們,給他們下跪,讓他們救活我媽。
早上還好端端的媽媽,轉眼就被推進了手術室,我簡直無法接受,內疚壞了。
如果我媽還在重慶,還打著麻將,喝著茶,也許她就不會倒下,如果我爭氣,嫁了好人家,有個好婆婆,也許就不用我媽擔憂,如果我再努力些,衣食無憂,請得起好保姆,也許我媽就不會……
說到底,我媽都是為了我,年輕時為了我孤獨一生,老了還為了操碎了心,如今把命都搭了進去。想到這裡,我無法自己。
曾凱接到我的電話,急匆匆地跑來了,他抱著無助顫抖的我一個勁地安慰:「小潔,你別急,媽一定沒事的,相信醫生,你放心,媽的病,咱們肯定要管到底。」
他的話我聽進去了,可我顧不上那麼多,我在心裡一遍遍祈禱,祈禱我媽一定會度過難關。
手術持續了近八個小時,那期盼的燈終於滅了。
我一下子竄了過去,晃了一下,幸好有曾凱扶住,不然,滴水未進的我肯定會。
萬幸的是,手術非常成功。
我喜極而泣,抱著曾凱一頓亂捶。
雖然出了手術室,可並沒有脫離危險,我媽隨即被轉移到ICU病房。
因為植入了三個支架,這一切都得看我媽的造化,看有沒有排異,具體恢復情況還真不好說。
聽完醫生的一席話,我剛放下的心又懸了起來,我揪著醫生,懇求她給我媽用最好的藥:「只要能救我媽,花多少錢我都願意!」我那企求的眼神恐怕只有經歷過的人才懂。
曾凱也在一旁附和著,但明顯底氣不足,說話都打了啃吧,那一刻,我哪裡知道他為了我媽已經山窮水盡了。
我眼裡只有病床上的媽,其餘的一切都是曾凱在打點。做個大手術花錢如流水,根本不是我們能頂住的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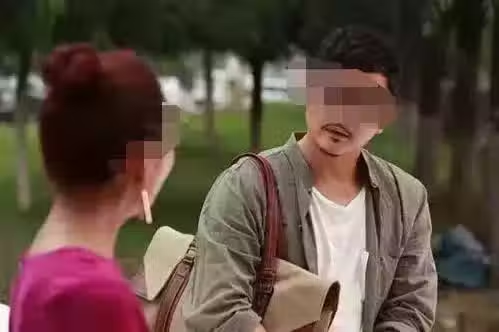
我媽一直都沒有穩定的工作,前些年,才辦了城保,這異地出了事,估計也得先行墊付,就是之後有報銷,也不會拿回多少,大頭子還得自己扛。
那一刻我才意識到沒錢看病的滋味有多難熬。
曾凱臉色很不好看,我知道他也著急,可我只能指望他了,我媽的一線生機全握在了我們倆的手上。
我媽進手術室前,曾凱就已經繳了10萬塊,一場手術下來,這些錢已所剩無幾。
可如今又進了ICU,那一天的費用都高得嚇人,真的不是我們這些普通家庭可以承受的。
等待的過程中,曾凱啥也沒說,我知道他也在默默祈禱我媽能早日出來,否則那就是個無底洞。
我和曾凱都來自普通人家,我們在這座城市裡,算得上白手起家,自力更生。
他一個人的工資,不僅要還車貸房貸,還要奶孩子,可如今還得支付我媽那高昂的住院費。
我媽這一病,簡直要了我們的命,掏空了家底不說,還欠了一屁股的外債。
可祈禱了半天,也沒有盼來奇蹟,我媽的病情急轉直下,出現術後肺部感染,直接上了呼吸機。
我一下子傻眼了,哭得稀里嘩啦,揪著醫生求救命,可還是無濟於事。
看到病危通知單的那一刻,我幾乎要暈死過去,再看到那一沓催款單,我更是不敢直視。
我看到了曾凱那蒼白的臉,我知道他已經快走投無路了,紅腫的眼睛,明顯是偷偷地哭泣過。
我媽在ICU住了十來天,加上手術,前後已花去近三十萬。
對於有錢人,可能是毛毛雨,可對於我們倆簡直可以說是天文數字。
那一刻,我知道曾凱真的已經彈盡糧絕了,因為他的幽默、他的油嘴滑舌早沒有蹤影。

 武巧輝 • 61K次觀看
武巧輝 • 61K次觀看
 燕晶伊 • 79K次觀看
燕晶伊 • 79K次觀看




















